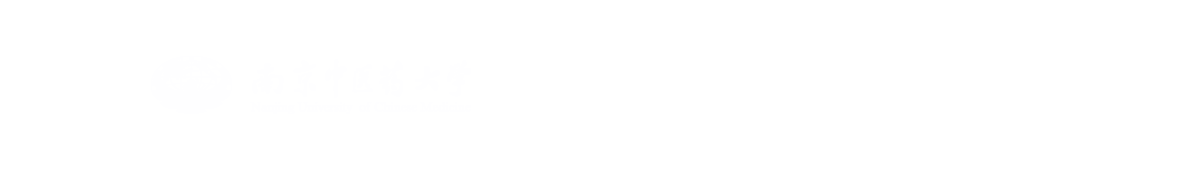十分文章七分改。没有改不动、改不好的文章,只有不想改、不肯改、不会改的人。学习写作,学会修改是必不可少的。掌握了修改之法,就意味着多了一项写文章的本领,多了不少出精品的可能。
修改,是写文章的一个重要环节,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。古今中外,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,都非常重视修改、善于修改。
名家修改文章,除了个性化的方法和习惯,普遍有这么一些共性特点——
一是标准高、尺度严。高标准才有高质量,严要求才能出精品。真正的文章高手,心里都有一把精密度很高的尺子,他们的眼睛就是一台高倍数的显微镜。一篇在常人眼里还蛮不错的稿子,用他们的尺子量,就不一定合格了;他们的眼睛只要一扫过去,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纤毫毕现、无处遁形。
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,被誉为“中共中央一支笔”的胡乔木修改文章堪称一绝。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送他审阅的稿子,一般都用8开新闻纸,当中只排印3栏长的文字,周围留有很大的空白,以方便修改。胡乔木改稿子的时候,从选题到立论,从标题到全篇,从理论到政策,从观点到材料,从谋篇布局到层次结构,从引语数字到标点符号,凡是有什么毛病、偏差和欠缺,很难逃过他的“火眼金睛”。他对文稿的每一个概念、判断和推理,每一个表述和提法,都力求准确、恰当、贴切、得体,合乎政策,合乎实际,合乎逻辑,合乎分寸。正因为如此,周恩来总理评价说:“许多文件只有经过胡乔木看过,才放心发下去。文件经过胡乔木修改,就成熟了。”
二是不怕烦、反复改。俗话说:“米淘三遍沙粒少,文改数遍质量高。”清代文人袁枚诗云:“爱好由来落笔难,一诗千改始心安。”(《遣兴六首》其五)很多写作大家都有不随意将过程稿示人、不轻易定稿的习惯,对自己的稿子总是改了又改、精益求精。俄国作家果戈里主张文章最好有8次修改。托尔斯泰的巨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写了5年,仅开头部分就修改了20次。胡乔木主持起草中央重要文稿,经常反复改上几十遍甚至上百遍,在排印过程中还打电话修改某些句子和提法,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让印刷厂改动,直到正式付印为止。
三是动刀狠、肯割爱。刘绍棠的长篇小说《地火》定稿时有50万字。当时,许多出版社争着向他索稿,可刘绍棠却迟迟没有交稿,他说:“再删一回,争取更少浪费一点国家的纸张、工人的劳动、读者的时间和金钱。”经过两次大的修改,他主动删去了20万字。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《杜鹃和雄鸡》,初稿有200多行,发表时只有21行。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中篇小说《老人与海》,前后删改了200多遍,最后只留下原稿篇幅的十分之一。
名家修改文章,一篇文章的所有构成要素都在修改范围之内,既不怕伤筋动骨、不惜推倒重来,也决不放过一个词、一个字、一个标点上的小毛病。
——托尔斯泰创作小说《复活》,前后整整十年,几轮修改的重点都是升华主题。
——田汉修改话剧《关汉卿》,根据郭沫若等的意见,把剧本由原来的9场扩大为12场,并相应增加了人物和事件。这是结构上的调整和变化。
——魏巍在撰写通讯名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之前,曾写过一篇《自豪吧,祖国》的通讯,里边写了20多个他“认为最生动的例子”,“由于例子堆得多,好像记流水账,哪一个也不充分”,后来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一文只用了3个最典型、最感人的例子,却成就了一篇红色经典。这是素材上的修改。
——钱钟书的《围城》作过多次修改,内容变动多达上千处;鲁迅逝世前几天还在精心修改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一文,变动有60多处。这些都是综合修改。
至于文字上的精雕细琢,例子就更多了。在我国文学史上,贾岛用心“推敲”诗句,齐已拜郑谷为“一字师”,王安石把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中的“绿”字改了十几遍才定下来……这些典故,与主人公的作品一样熠熠生辉。
法国作家福楼拜改稿尤为认真,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。一天,莫泊桑带着一篇新作上门请教,看见福楼拜的书桌上每页稿纸只写一行,其余几行都是空白,很是不解。福楼拜笑了笑说:“这是我的习惯,一张十行的稿纸,只写一行,其余九行是留着修改用的。”据说,福楼拜特别讲究文章的字眼,写完以后还要用钢琴来检查,听一听声音是不是和谐。
为什么这些名家大师如此重视文章的修改?作家秦牧曾一语道破“天机”:“修改,并不是消极的‘改错’而已。它也是又一次的积极的‘创作’。”